
作者丨刘主权

对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研究的深入,有必要着眼于具体的作品类型。影视作品是公众文化娱乐的重要对象,但各方对影视作品合理使用的认知理解存在割裂与隔阂。判断对影视作品的使用是否成立合理使用,需要考察使用版权影视作品行为的性质和目的、被使用版权影视作品的性质、使用版权影视作品的数量与实质、使用行为对影视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以及影视作品的目标受众、素材获取、创作方式、表现形式、题材类型等要素。
01
引言
2021年4月9日,70余家影视行业协会、影业传媒公司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尊重版权,未经授权不得对影视作品实施剪辑、搬运等行为;4月23日,众影业公司联合500余位艺人再发倡议,呼吁短视频平台规范版权,倡导公众账号运营提升版权意识;4月28日,国家电影局发文“坚决整治未经授权剪辑、传播他人电影作品的侵权行为”[1]。从2018年6月至2020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数由5.9亿增长至8.7亿[2],短视频承载高密度信息量、契合时代碎片化娱乐方式[3],影视作品是公众文娱重要对象,影视解说短视频自然风靡。此声明矛头直指未经授权的复制、剪辑、传播等行为,而该行为成品以影视解说短视频为典型,普通公众潜意识中认可该行为的合理性,二创者以“合理使用”自居,此类案件被告也必然提出合理使用抗辩。对于版权维权与官方态度,纵观舆论,多有不解与诘问,各方对合理使用的认知存在割裂与隔阂。自1990年9月至2018年10月,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相关研究成果在CSSCI数据库中收录7461篇[4],相比之下,对影视作品这一具体作品类型的合理使用判断研究则显得相形见绌,于今境况,有必要对如何判断影视作品的合理使用作进一步探析。
通观世界,对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判断方法并不单一[5],但实际所要考察内容大体相同,各方法之间存有共通之处与融合之势。对合理使用的判断主要包括“规则主义”与“因素主义”,前者以“三步检验法”为典型,后者以“四要素法”为代表。我国关于合理使用的规定,2020年《著作权法》修订,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1条纳入《著作权法》第24条[6],实际吸收了“三步检验法”的内涵;最高人民法院[7]则认可了美国的“四要素法”[8],亦有关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该方法适用的实证研究[9]本文拟以“四要素法”为基础,分析对影视作品合理使用的判断。

02
使用版权影视作品行为的性质和目的
对使用行为性质与目的之讨论,常陷入“转换性使用”之中,此概念源于美国,有实证研究表明美国法院对其重视程度[10]。但在引入过程中存在概念认知争论、释法路径不当,实际运作过程并不流畅[11],有观点认为,“转换性使用”实为判决结果合理化的说理帽子,并非案件分析的合适工具,转换性使用不具转换性[12]。综合“规则主义”与“因素主义”观之,实践中一般认可“欣赏、批评[13]、研究、教育、公务、公益、慈善”等行为的合理性,合理使用行为性质与目的中的积极要素,不妨总结为“正当性”,虽稍显宽泛,但胜在包容,大可不必挣扎于“转换性”的概念中。
使用者的行为是否属于“商业性使用”历来是讨论焦点,实践中的商业性使用往往足以否定合理使用,从谷阿莫“X分钟带你看完XX电影”[14]到人人影视字幕组[15],再到如今一些切条搬运者竟也挂上“解说”之名,基于强烈的商业性[16],无法成立合理使用。传统观点认为凡商业性使用必非合理使用[17],但如今看来,此观念有必要更新,Google library案[18]、Kelly缩略图案、Black网页信息临时复制案,美国联邦法院明确传达,商业目的并非当然排除合理使用[19]。
更深层次的,还涉及文化权力空间的开拓乃至时代话语权的争夺。影视创作技术的精化与影视解说者的泛化冲突剧烈。影视解说对观众价值观的塑造力,在某些程度上并不逊色,甚至超过影视原作。一些知名影视解说者对影片的解说评价甚至对其后续市场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
对该要素的判断,实际中使用行为的性质与目的未必单一,兼备正当性与非商业性时,可契合该要素,但同具正当性与商业性时,实则涉及著作权法双重目的之权衡,常需个案分析[21]。
03
被使用版权影视作品的性质
相对其他要素,既有文献对此要素的分析明显较少,研究一般从作品内容、作品类型入手,多局限于区分作品是否发表、虚构或纪实的讨论[22]。
本文认为,针对影视作品有必要关注以下问题:(一)影视作品的目标受众。例如创作者本就意在将其作品受众特定化为学校、学生时,此经营方式下(以教辅资源为典型),则不宜认可为教育而使用具有目的正当性;(二)影视作品的素材获取。需考察素材取得难易,观赏者聚焦于作品的呈现效果,但对某些难以获得、昙花一现的视听素材,其取得可能比呈现更具难度[23],此情形下适用合理使用应当更为严格;(三)影视作品的创作方式。影视作品的角色选择、取景、构图、镜头机位、配音配乐等制作方式与拍摄手法不容忽视,对影视作品的合理使用判断应严于文字作品,亦符合国际对视听作品合理使用的判断严于印刷作品的做法[24];(四)影视作品的表现形式。印刷技术是文字、符号的表达,是概念文化时代。而影视则创造可见的人,是视听文化时代[25]。影视作品不同于文字作品,影视与文字经不同的方式表达其背后思想与情感,从剧本文字到视听影视,契合公众阅览喜好经历文字、图片、视频的发展与融合,笼统而言,动态画面相较静态文字更符合公众的娱乐方式,换言之,即具更高的吸引力,对影视作品合理使用的判断有必要严于文字作品。(五)影视作品的题材类型。不必从电影学视角精细分类,基于现实国情,是否有可能期待对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合理使用判断,赋予更高包容度。此外若写实题材实际反映的是当下社会热点,当所传达信息与公众高度关注的问题有关时,合理使用的范围无疑会扩大[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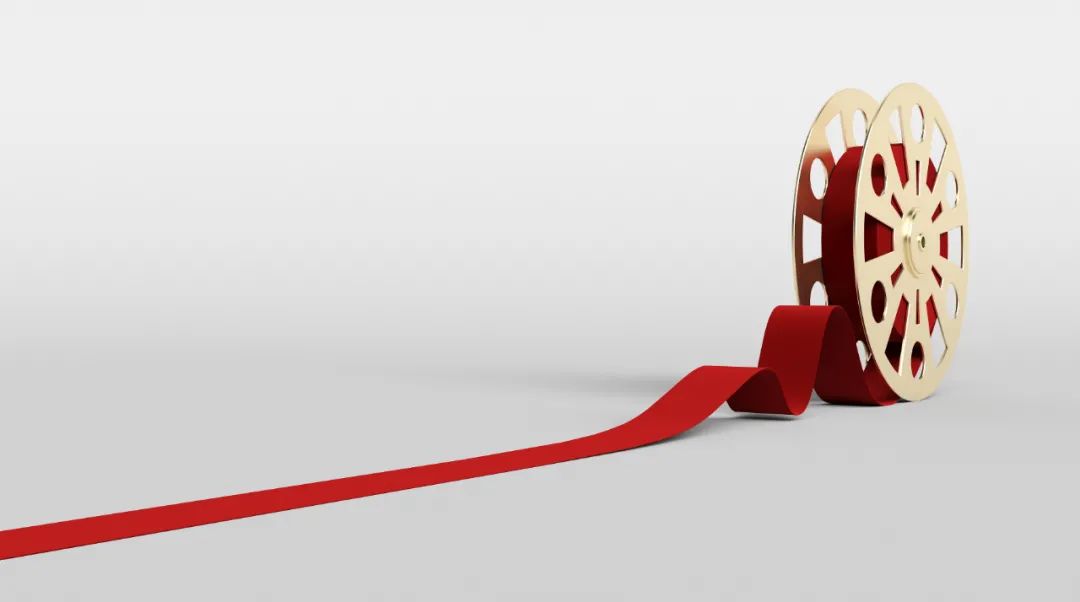
04
使用版权影视作品的数量与实质
一般而言,使用他人作品的篇幅数量与判断合理使用的严格程度呈正相关。国内外曾有关于合理使用中适当引用的具体数量(字符字数、影视时长)规定[27],可称为绝对数量标准;相对数量标准(比例标准)亦同时适用,被控侵权人辩解侧重于使用部分在被控侵权作品中的比例,权利人则关注使用部分在权利作品中的比例,法院认为重点并非使用部分占权利作品比重大小,而是该部分占被控侵权作品的比重[28]。限定绝对的数量或比例并不合理,合理使用所允许使用影视片断的长度和比例, 应当取决于正当目的合理需要[29]。
对数量的考察只是辅助,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使用了权利作品的实质部分。影视作品版权人往往难以容忍他人肆意使用权利影片中的“高光时刻”。使用数量、比例多少与合理使用并无必然联系[30],在Columbia公司被权利人起诉使用“卓别林”系列影视作品一案中,美国法院从1小时29分钟的影片析出实质重要的55秒[31]。短视频不因其短而不构成作品[32],使用行为未必因时长之短而合理。在“图解《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案”中,被告辩称“按一般类电作品每秒24帧计,涉案图片仅引用原作0.5%的画面”,但法院认为通过300多张图片连续放映,能够迎合用户短时间获悉剧情、画面内容的需求,不能构成合理使用[33]。影评作品往往需要介绍影视作品,再现部分画面以进行评述,但本案图片集几乎全为原有剧集已有表达,故不能成立合理使用。
使用者期待降低合理使用的门槛,权利人希望严格适用合理使用制度,看似方向相反,背后的利益逻辑实则一致。将问题推向极端,版权人是否可以主张影视作品中每一帧画面的专有权?在“《产科医生》海报、剧照、截图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法院作出了否定回答:涉案截图为从剧中连续动态画面截取的一帧帧静态画面,数量有限,截图组合亦无法表达完整故事,公众难以经由欣赏截图获悉影视作品全部内容,故截图的使用未实质再现涉案影视作品[34],可构成合理使用。

05
使用行为对影视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
在知识产权去人格化背景下,该因素有成为判断合理使用的最重要因素之趋势。亦有学者建议,对合理使用的判断,需回归以市场为中心[35]。使用者是否侵权与版权人是否维权是两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体性使用比之群体性使用,小范围使用较之大范围使用往往较少陷入纠纷之中,因为权利人大多容忍不影响其市场利益的使用,即使权利人认为他人属于“侵权”,影视作品的权利人或可接受某些“影视解说者”代为输出影片价值观,但想必难以容忍他人剪辑、传播的行为影响其最终票房收益的结果。法院的说理综合考量各种因素,而往往最终落脚点为“使用行为对影视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在我国首例图解电影侵权案中,被告于其网站标示“十分钟品味一部好电影”,并且提供《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剧集截图382张,浏览者可以反复播放,法院认为涉案截图覆盖剧集主要画面、剧情,并非仅供宣传。引用超过必要限度,损害原作正常使用,对其市场价值造成影响、替代[36],不能构成合理使用。
甚至可以该要素推定使用行为的性质与目的是否正当、引用程度是否适当等因素。以影视解说短视频为例,为介绍、评论、说明而引用他人作品,被引作品应为论据、例证以说明某问题,在解说者作品起辅助作用,使用影视作品部分不应是解说短视频吸引观众的主要原因[37]。针对电影解说短视频的自然人创作者个人直接起诉的还未见案例,如今以倡议书形式呼吁社会尊重版权,实则是影视版权方在维护版权与维系粉丝之间的利益衡量,目标还是在于维持其市场利益。《2021年中国短视频版权保护白皮书》将二创短视频分为六类,其中预告类、影评类、盘点类属于中低风险版权侵权,片段类、解说类、混剪类属于高风险[38],该分类标准所侧重的实际还是短视频对原影视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
06
结语
判断合理使用要素之间的关系并非累积适用,需进行整体考量[39]。对合理使用的判断事实上需要考虑与案有关的全要素,四要素法从众多典型争议中归纳出焦点有其进步意义。影视作品合理使用的具体判断中,若是在各要素评价中都能得到正面反馈,无疑能够极大地增强论证合理使用的说服力。但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各要素在正面反馈与负面反馈间排列组合,司法机关需要在各要素之间反复衡量,不仅在适用合理使用制度,也在发展和完善该制度。
《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明确表明其双重目标,但双重目的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可以说,合理使用制度正是为平衡调节各方利益而生。合理使用的模糊性常受诟病,但从反面来说,这倒正是其魅力所在。利益平衡堪称现代知识产权法基本理念[40],从传统时代到“众媒时代”,合理使用的具体判断标准与尺度经历发展流变,但背后利益平衡的思想一以贯之。作品兼具私人品格与公共品格,立法者需要关注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公众需要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法律需要注意权利的有效性与有限性,对著作权的保护与对著作权的限制同等重要[41]。而若以抽象的理论界定合理使用遭遇瓶颈,便有必要在现实案例中抽丝剥茧以完善理论,而这亦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分化与融合。
# 注释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