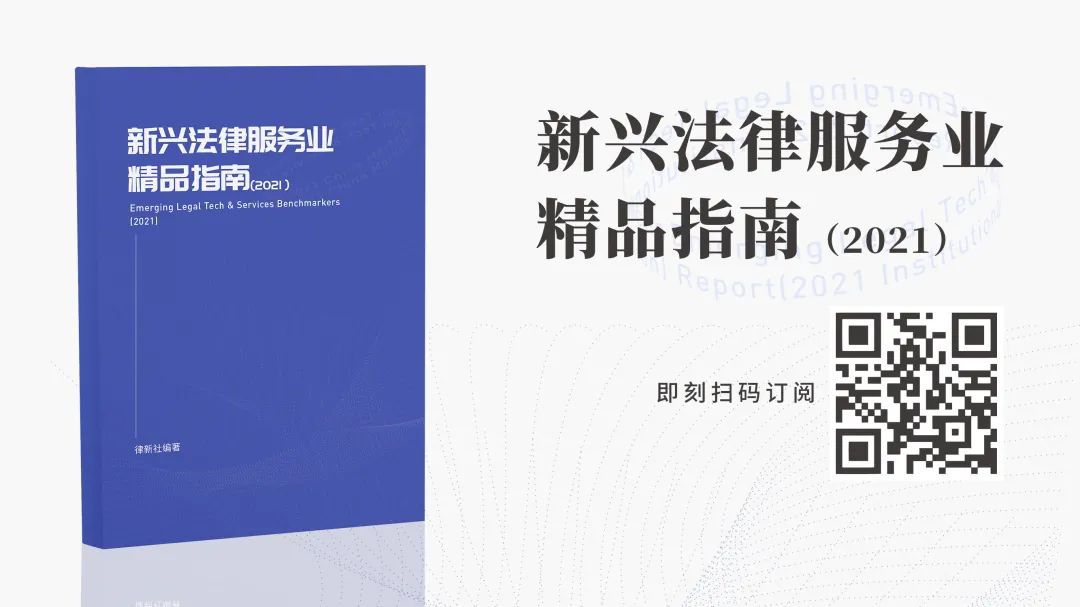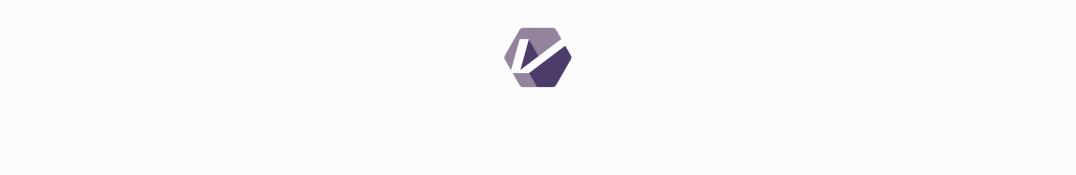

作者丨张祖增
噪声污染防治是重大的民生保障问题,《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是我国噪声污染防治的坚实法律基础,也是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必要法治保障。但当前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立法存在法律名称与传统环境要素污染立法形式上不对称、生态化理念缺失、环境噪声侵权归责原则适用混乱、噪声内涵界定过于狭隘及噪声污染衡量标准缺乏合理性等问题,这导致现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不能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需要。2021年8月,《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订工作已经提上国家立法机关议事日程并于近期完成一审稿审议工作,针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订与完善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相关立法内容,笔者拟从法律名称修改、立法理念确立、噪声法律内涵界定、归责原则适用及噪声污染侵权认定标准完善等几个方面谈谈新时代我国噪声污染治理的法律改革之道:
01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以健全的生态法律制度为保障,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从生态环境立法的整体主义来看,我国除了对自然资源与生态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外,我国生态法制还包括防治各种污染物排放的法律制度,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土壤污染和环境噪声污染,这五大污染类型构成我国污染物防治立法的主体。然而,通过检视其他四大污染物防治法律规范,在立法名称的表述方法上,1997年颁布实施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与1995年通过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1984年通过的《水污染防治法》、最新颁行的《土壤污染防治法》等其他环境要素污染立法存在明显的法律名称表达、形式结构的不一致性。
由于法律规范的表达形式事关法律体系的科学建构,并实质影响法律的内容编排,所以“环境噪声污染”的表述带来最直接的问题是:一方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法律表达形式会导致我国整个环境要素污染防治立法体系缺乏逻辑严谨性、各项立法名称的形式选择存在严重不一致性;另一方面,立法名称的编排与选择是法律内容外在表达的形式写照[1],此法律文本的名称设计会使得社会公众对噪声污染来源产生歧义认识,从而影响噪声污染防治立法内容的周延性与科学性。因此,应在形式理性指引下,统一各环境要素污染立法的名称表达方式,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法律名称修改为《噪声污染防治法》[2],将法律规范的对象明确限定在“人为噪声”这单一污染要素上,保证噪声污染治理的针对性,最终实现所有污染防治法律规范名称表达的形式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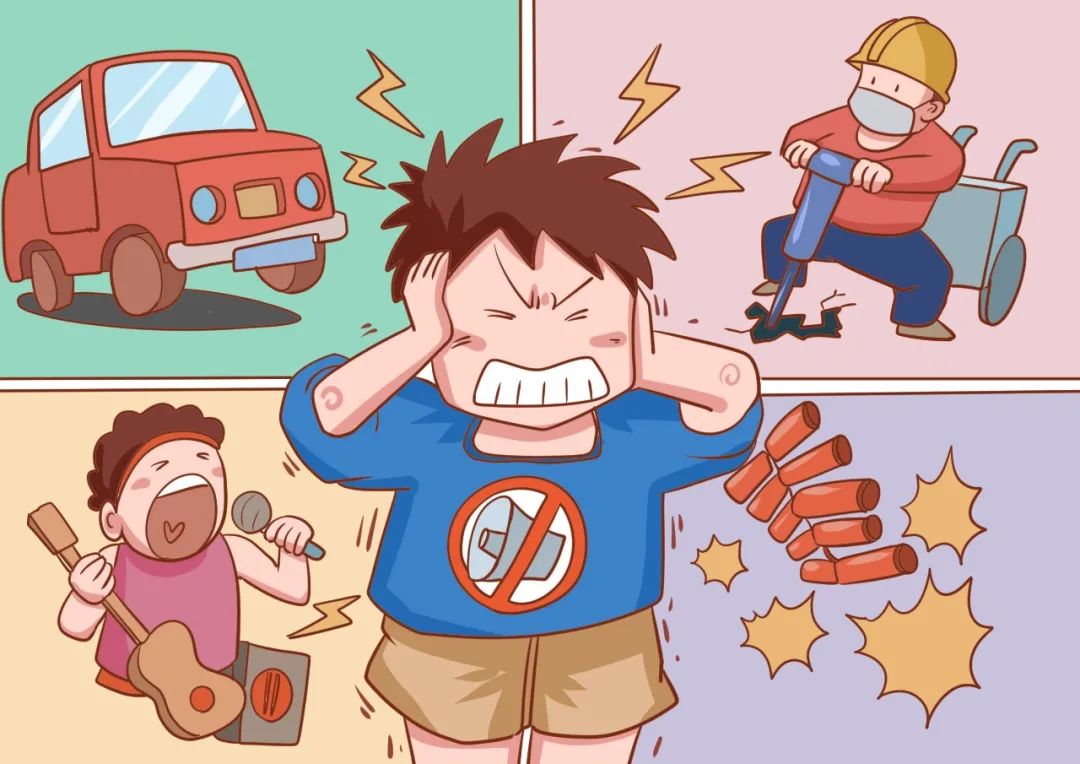
02
环境法发展到今天,保障人的人身和财产不受来自环境中有害因素的伤害仍然是环境法的首要任务,但在环境危机日益加深的时代主题下,这并不能说明生态环境本身的利益就该退而求其次予以维护。审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可以发现,噪声污染防治立法生态化理念长久缺失,生态文明建设的立法目的尚未确立,纵观整部立法,其为浓厚的“人本主义为主”所笼罩,以崇尚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要立法指导思想的自然伦理观一直未能得到立法者应有重视,此问题主要体现在立法对“环境噪声”内涵界定过于狭隘、噪声污染防治对象太过单一两方面。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2条第1款规定:所谓环境噪声,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此规范设计的一个明显漏洞在于,其仅仅将“噪声”定义为一种“干扰人们生活环境”的声音,并未在“噪声”定义中涵盖影响“生物生存发展”的声音。由此一来,该条第2款对“噪声污染”法律概念的界定仅限定在“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事实上,噪声污染除了会对人类产生危害,其同样也会对生物物种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噪声对动物的侵扰主要体现在:高分贝声音会危害动物生命健康,如上文所述其会对动物的听觉、视觉、内脏器官和神经系统造成伤害;一些野外的噪声源,如工业生产、交通建设与运输等,也会惊扰到野生动物,干扰它们的捕食、求偶、筑巢等生物行为,侵害它们的栖息环境,迫使它们寻找新的生存家园。《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虽在此次修订中规定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立法目标,但文本对噪声的定义仍将“生态环境保护”排除在法律内涵之外,这使得生态文明建设的立法目的流于形式,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系统立法保护。因此,建议在立法修订时,考虑噪声对物种的影响,丰富噪声法律内涵,将除人之外的生态环境纳入噪声定义之中。
此外,现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在噪声污染防治对象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在现有条款均是为城市噪声污染治理而设计,农村地区噪声污染问题未能纳入立法规制。现行噪声法第12条、第19条、第23条、第28条、第29条、第30条、第33条、第34条、第35条、第37条、第39条、第42条等十余个法律条款均对城市噪声污染防治作了系统规定,体现出现行立法典型的城市噪声污染治理的整体立法思路。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城乡二元化发展模式的破除及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向农村的延伸,噪声污染表现出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趋势。同时,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基础较为薄弱,比如没有对声环境功能区进行明确划分、农村地区噪声监测设备设施建设不足、农村噪声污染的补偿标准还没有统一等[3],这表明农村地区噪声污染治理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亟需为农村地区噪声污染治理提供必要法律保障。建议扩大噪声污染防治地域范围,将原法中“城市市区”的限定删除,从而将农村噪声污染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为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噪声污染治理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
03
归责原则是侵权责任评判的核心议题,反映出立法者对侵权行为的价值认知,是侵权责任的客观构成要件之一。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归责原则一直奉行“无过错原则”,我国国内有关法律规范对该原则的适用也进行了立法确认。2010年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环境保护法》以公法视角对环境侵权无过错归责原则的适用作了法律强化,其中第64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229条在环境侵权责任认定上同样继承了《侵权责任法》对归责原则的属性规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Ⅰ]第1条对环境侵权责任的无过错性质也作了细化规定,强调“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不论侵权人有无过错,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人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环境噪声污染作为环境污染侵权的“种属概念”,在普通环境污染侵权适用无过错原则的立法背景下,噪声污染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就具备了逻辑上的必然性。
遗憾的是,我国噪声污染无过错责任原则仅停留在理论认知层面,我国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形成环境噪声侵权“无过错归责原则”统一适用的局面。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发布的10起典型环境侵权案例中,“沈海俊诉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即是适用环境污染侵权过错责任的典型例证[Ⅱ]。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其认为:与一般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不同,环境噪声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要件之一是主观存在过错,而判断侵权行为人是否具有噪声排放过错的依据在于是否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即采用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2条对“环境噪声污染”认定的行为模式——“超标排放噪声+损害后果”,主张“只有超标排放环境噪声且造成他人损害的才能承担噪声污染责任”。然而,出于对污染受害人利益维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考量,此案例在噪声污染侵权之归责原则适用方面,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如果只有超标排放噪声且造成他人损害的前提下才能苛责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带来的一个很大问题是,许多达标排放噪声的污染行为因不具有“排污过错”而具有非可责难性。换言之,达标排放噪声的行为会有效阻却了噪声污染侵权责任的承担,因此,从分配正义角度出发,为保证噪声污染发生后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法律救济[4]、促使排污者尽到对自己排污行为对环境所产生不利影响的谨慎注意义务,建议在修改噪声法时,明确无过错责任在噪声污染归责原则适用中的法律地位,实现其从司法实践中过错归责原则向一般环境侵权无过错原则的理性回归。

04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2条采用了“噪声排放标准”作为噪声污染事实认定的法定依据,对这一污染的判断标准,噪声法规定了较为完备的配套法律规范,如第23条规定:在城市范围内向周围生活环境排放工业噪声的,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第28条规定:在城市市区范围内向周围生活环境排放建筑施工噪声的,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第43条规定:新建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的边界噪声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以上条款架构起噪声排放标准与噪声污染的内在逻辑关系。然而,检视“污染物排放标准”与“环境污染”的法律内涵可知,环境质量标准在判定是否存在环境侵权中往往起着更重要作用。所谓“污染物排放标准”是指为了实现环境质量标准并在环境质量标准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技术水平等因素而确定的排污者在排放污染物时应当遵守的基本指标。据此可知,环境质量标准的实现才是环境法最深层次的价值追求,污染物排放标准只不过是实现环境质量目标的一种手段[5];而所谓“环境污染”是指超过某一环境要素的自然承载力或净化能力而造成的环境品质恶化的一种损害结果或实然状态,而评判环境品质恶化的基本依据便是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相反而不是污染物排放标准。例如,在水污染防治领域,衡量水污染与否的标准是水环境质量标准,而不是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因此,将噪声污染排放标准作为判断噪声污染侵权的法律依据,既不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设定的价值追求,也背离了“环境污染” 的本质属性,特别是在合法的噪声排放行为可能造成声环境质量超标进而危害他人健康的背景下,坚持适用噪声排放标准来认定噪声污染侵权,就会使受害人处于合法权益无从保障的尴尬境地。
此外,《声环境质量标准》[Ⅲ]作为指导环境立法的技术性规范,其立法目的“保障城乡居民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声环境质量”也表明,只要声环境质量达标,就能满足相应声环境功能区的正常用途,保障城乡居民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对声环境的要求,从而不存在噪声污染问题。相反,只有行为人排放的噪声超出声环境质量标准,且影响到他人学习、工作、生活等合法权益的,才可能被认定为存在噪声污染侵权问题。因此,噪声污染认定的标准应转向“声环境质量标准”,建议将“噪声污染定义”修改为“所产生的噪声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声环境质量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以及影响生物生存发展的现象”。
05
未来修法时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将噪声污染防治立法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通过“生态优先原则”的确立、“公众参与原则”的引入以及“风险预防原则”的设定,结合敏感点噪声控制制度、产品噪声名录制度、噪声污染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具体制度的实施,从立法理念的生态化、名称表达的统一化、噪声污染定义的科学化以及侵权归责原则回归的理性化出发,构建满足公众美好生活需要、涵盖物种利益保护的噪声污染法律治理网络,最终实现我国噪声污染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