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会万方友!“律新社书友会”每周推出法律人的好书推荐和读书心得,分享让人心动的智慧。
这两天,大成律师事务所蔡正华律师新书《为“坏人”说话》面市,这是法律人第一本通过众筹出版的书。这里面有什么故事?请看律新社与蔡正华律师对话。如果你有好书出版,或者有好书推荐,欢迎和我们联系。
律新社 | 孔冰欣
当我还是个“文萝”(文艺小萝莉)的时候,曾因黄仁宇先生的一番评议备受震动: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缺乏数目字管理。极有意思的是,律新社的老友蔡正华律师,在接受本社专访时传递了类似的信息。
老蔡刚出了本新书《为“坏人”说话》,乍看难免有“标题党”之嫌,不过作者真正想表述的思想无比严肃认真:“国人常以好、坏这样的形容词轻言是非论断他人,可是,这只不过是道德范畴的概念,我极不赞同此等意义的人群划分。”
以犀利之言辞,剖析“当下”之不完满;以理想之愿景,催化读者回归理性构建公民社会。老蔡没把自己局限于律师的身份,一心致力于成为新启蒙运动的先驱——你可以笑他观点幼稚,但不可否定他的情怀。或者,我们可以换个不恰当的比方——你可以痛斥瓦格纳的疏狂,但你不能忽视他天才的灵光。

Q1
最初写书的源动力在哪里?
蔡:写作是习惯,“写我所想”是夙愿。其实我很早就在《萌芽》上用笔名发表文章了,微信问世后,我发现这是个发表个人观点的极佳平台,所以“畅所欲言”了很多时事法律评论。而正如我在本书后记中提到的,促使我多写、乃至编撰成书的动力是想给女儿一份出生礼物。招远事件发生后,我意识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危险——黑暗、丑恶的东西居然在青天白日、众目睽睽之下肆意践踏光明;难道我们的孩子不该在一个更温暖、更有人性的环境下健康成长吗?身为人父,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呼唤社会正能量,呼唤公民精神。于是我开始联系出版社筹划出书具体事宜,刚好自己认识邓子滨老师《斑马线上的中国》一书的编辑,对方非常愿意帮我出书,对接后我更有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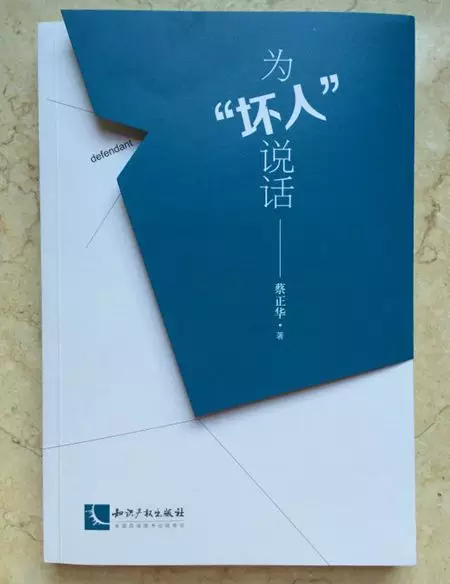
▲蔡正华律师新书——《为“坏人”说话》
Q2
本书主要内容是?请耗费口水具体介绍下。
蔡:事实上,这本书的内容挺简单,大概收录了我对2014年度热点法律事件、包括其它一些新闻大事件的独家评论,每篇文章切入角度、侧重点有所不同,涵盖法治理念、社会学解读、人性剖析零零总总等各方面。比如有对“疑罪从无”的个人看法;有对《十二怒汉》、《辩护人》等经典之作的影评;有对秦火火怎样一路“火”到审判席上的议论……其中有两篇是我最得意的:一篇是我为媒体写的元旦贺词《法律人,因为有梦想,所以任性前行》,一篇是我与检察官同学的信件往来互动。
Q3
你想透过本书传递何种信号、理念?
蔡:希望国人具备公民精神,人人心中皆有正义感,该出手时就出手,而这份正义感将成为大家共同的保护神。惟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让大家被我的文字激发出一种公民认同感,积极建设和谐社会。走自己的路,也让别人有路可走,这个世界不应该仅有自我、他我之分,人与人之间绝非止步于冰冷残酷的二元对立面。
Q4
本书题为《为“坏人”说话》,很有意思。在你看来,好人、坏人的界限如何划分?有纯粹意义上的好人、坏人吗?还是说,国人对好人、坏人的认识向来笼统而模糊,缺乏理性深刻的思考?
蔡:今年《新民周刊》的首期封面主题即是“为‘坏人’说话,口水中的刑辩律师”,当时我和周刊副主编杨江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此外,我还在去年专门写过一篇“我愿意为‘坏人’说话”的文章,这是否也算迎合了当下社会喜好搞二分法的标准?国人常以好、坏这样的形容词轻言是非论断他人,可是,这只不过是道德范畴的概念,我极不赞同此等意义的人群划分。复旦投毒案二审期间,我曾写过一篇“司法有二审,道德却只有一审”的文章,点击量破数万,据悉曾一度引发市委领导的重视。本人的核心观点是:简单粗暴地评议好坏是一大社会隐患,以道德划分人群,容易滋生伪君子与真小人,掩盖了我们真实而复杂的原貌。法律人发现事实、以事实为依据判定人;而先入为主,判断好人、坏人,再根据自己的判断寻找对号入座的“线索”,这属于感情用事,容易粉饰太平、掩蔽真理。一个人可能是道德层面的坏人,但他却做了事实层面的好事,何故民众在抨击其私德的同时,全盘否定其干实事的功绩?若单就政治因素或道德因素动辄横加批判,未免有失偏颇。让我深感遗憾的地方在于,这种埋伏在民族文化基因里的二元分法,导致矫饰与虚伪大行其道,还易酿成站队、分裂的悲剧。我国的司法机关、执法机构长期身处不可侵犯的神坛之上,其对立面进入司法程序后,往往便成千夫所指的“坏人”,而为“坏人”辩护的律师因此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可是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坏人”虽然不全是世俗意义上的“好人”,但也并非尽皆触犯法律的恶徒,律师只是恪尽职守为当事人服务罢了,“洗白罪犯”的误解请恕律师承受不起。
Q5
不少人觉得你的言辞太激烈,你认为自己是所谓的“愤青”吗?抑或是希冀通过犀利的文字、痛快的抨击,唤醒大众的法治意识,从而构建一个法律理想国?
蔡:词锋犀利胜于我者大有人在,文采不凡胜于我者亦大有人在。我不认为单纯“默默无声地理性着”与“咄咄逼人地愤青着”就能支撑起整个社会的进步了。实际上,我们在宣传时部分异化了真理,比如我们总说“一把筷子不容易折断,人多力量大”,但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一把筷子中的第一根筷子是怎么跳出来的,即领头人的问题,国家需要精神先驱。中国不乏老子、孔子这样奉行“无为”、“中庸”的思想家,但缺少伏尔泰、孟德斯鸠之类旗帜鲜明的思想家——他们是否都称得上某种特定意义的愤青?我觉得愤青这个名词如今已被诟病成“毫无建设智慧,只有革命勇气”一类的人物,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愤青不是为了破坏而破坏,而须破而后立。当然,肯定有前辈认为我的见解太过幼稚,但我至少提供了参考思路,并且愿意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从而做得更好。总之,我不会因为被当作是愤青而愤怒,坦白讲,我在自己的人生规划上并无太大野心,内心的诉求更超然些:政体与法律如果能让社会更美好,我便接受。有时候,犀利的语言是为了凸显观点的明确,我想让读者看清社会的不完美,然后为追求一份完美而共同努力。
Q6
本书原应是法律界第一本众筹成功的书,你是如何开展众筹行动的?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慷慨解囊?自己付出了多少?
蔡:我本人没花一分钱,我们起初便在网上发起了众筹项目,结果10天内众筹了3万元,最后顺利拿到出版所需资金。我非常感激读者的慷慨解囊,感谢亲友们的大力支持。我很欣喜地看到,本书有传播力、有市场,作者与受众间是相互满足的。而作为法律界首本众筹成功的书,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曾对此进行过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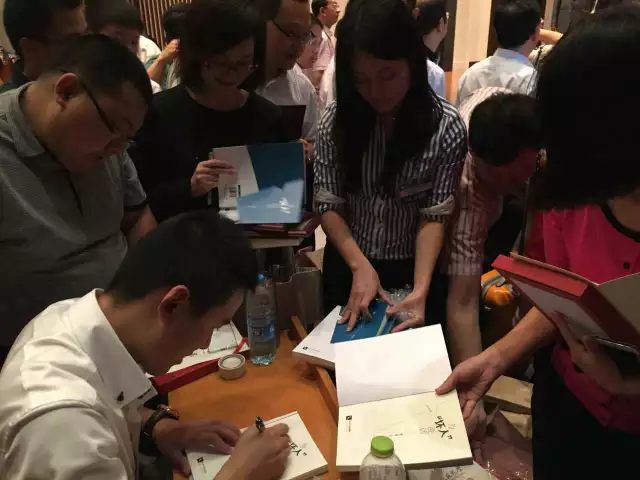
▲新书签售会
Q7
本书出版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蔡:部分所谓“敏感”文字通不过审批,一些我本人非常喜欢的稿件被删除了,可惜。如此一来,本书完整面貌、其思想体系无法得到如实呈现。
Q8
本书出版过程中,你也得到了很多法律人的支持,他们寄托了何种情怀?
蔡:物质上,他们给予了我近2/3的费用支持,大家理念相投,我说了他们表达不出、或不敢表达的话。精神上,很多朋友助我一起探讨、校对稿件,尤其刘桂明老师还作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序言,为此书增添光彩。我认为这些法律人和我一样,都希望律师这份职业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都希望社会回归理性本位思考问题,求同存异;都希望法治根植于每个公民的记忆里,道德教化不再试图捆绑法律。
Q9
你的本职是律师,却“不务正业”地喜好舞文弄墨针砭时弊、直抒胸臆,将来会继续写下去吗?
蔡:很庆幸,律师身份既为我提供了稳定的收入,也给予了我更多思考社会现状的契机。我认为,律师应该主动启蒙社会,启蒙大众理解法治。我曾给华政的杨新培教授写信,阐释一个国家仅凭坚船利炮不足以立民权、彰民法,唯有树立公民意识,法律方闪辉光。所以,我会坚持自己的价值理念,适时发表所见所闻所感。
Q10
你同时也是沪上非常活跃的法律媒体人,如何保证充沛精力,让自己在多个“战场”上游刃有余?
蔡:做律师,培训上课,做自媒体,写作……我所作的一切事情始终围绕着学习法律、使用法律、用法律服务社会的主线,核心目标统一,相互之间没有冲突,因此忙而不乱,不觉辛苦。这些工作是相互促进的,比如办案时我有新的思考与感悟,我会通过自媒体传播出去,然后接收社会反馈,了解他人想法,从而不断补充、完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