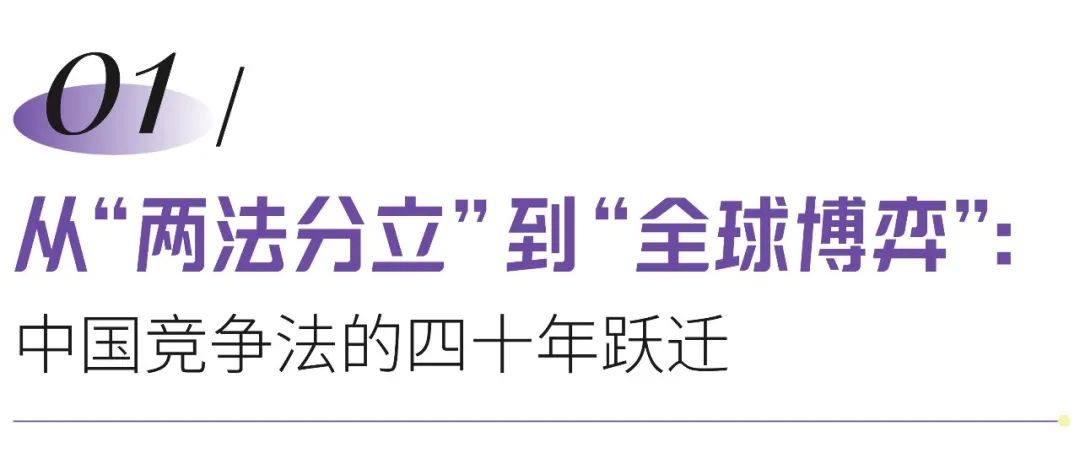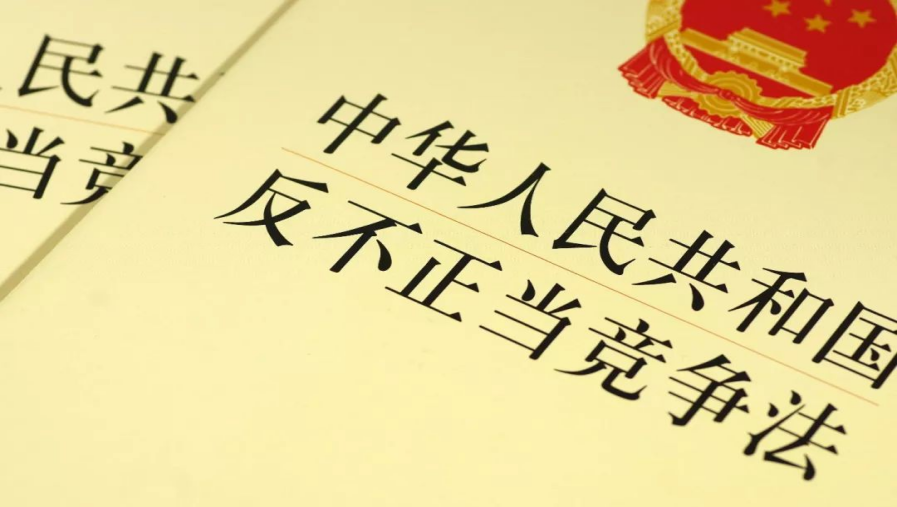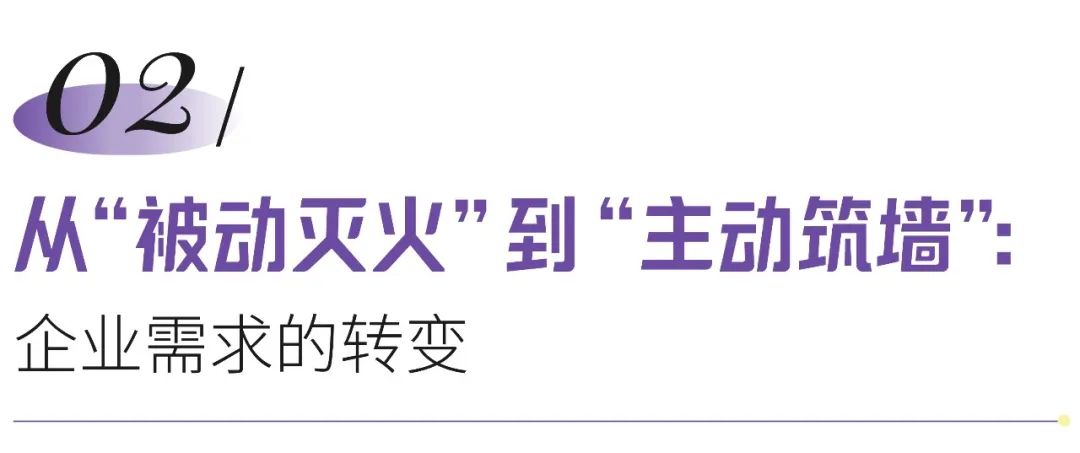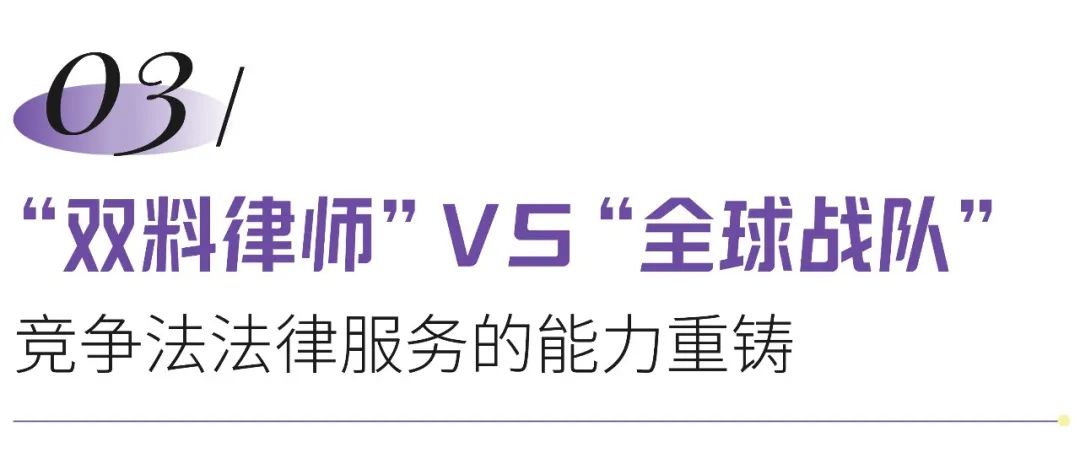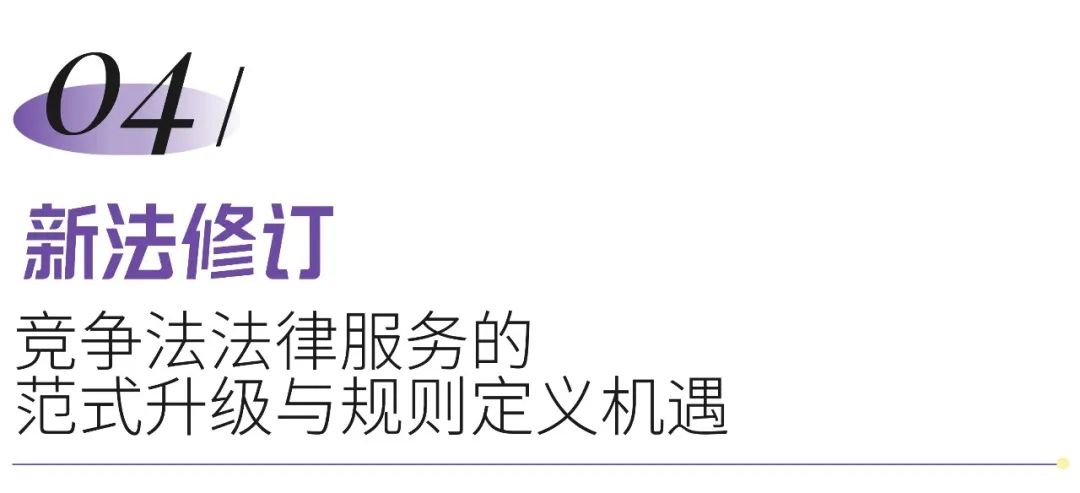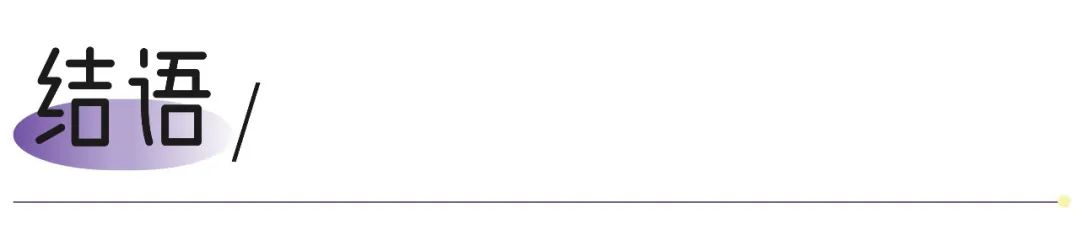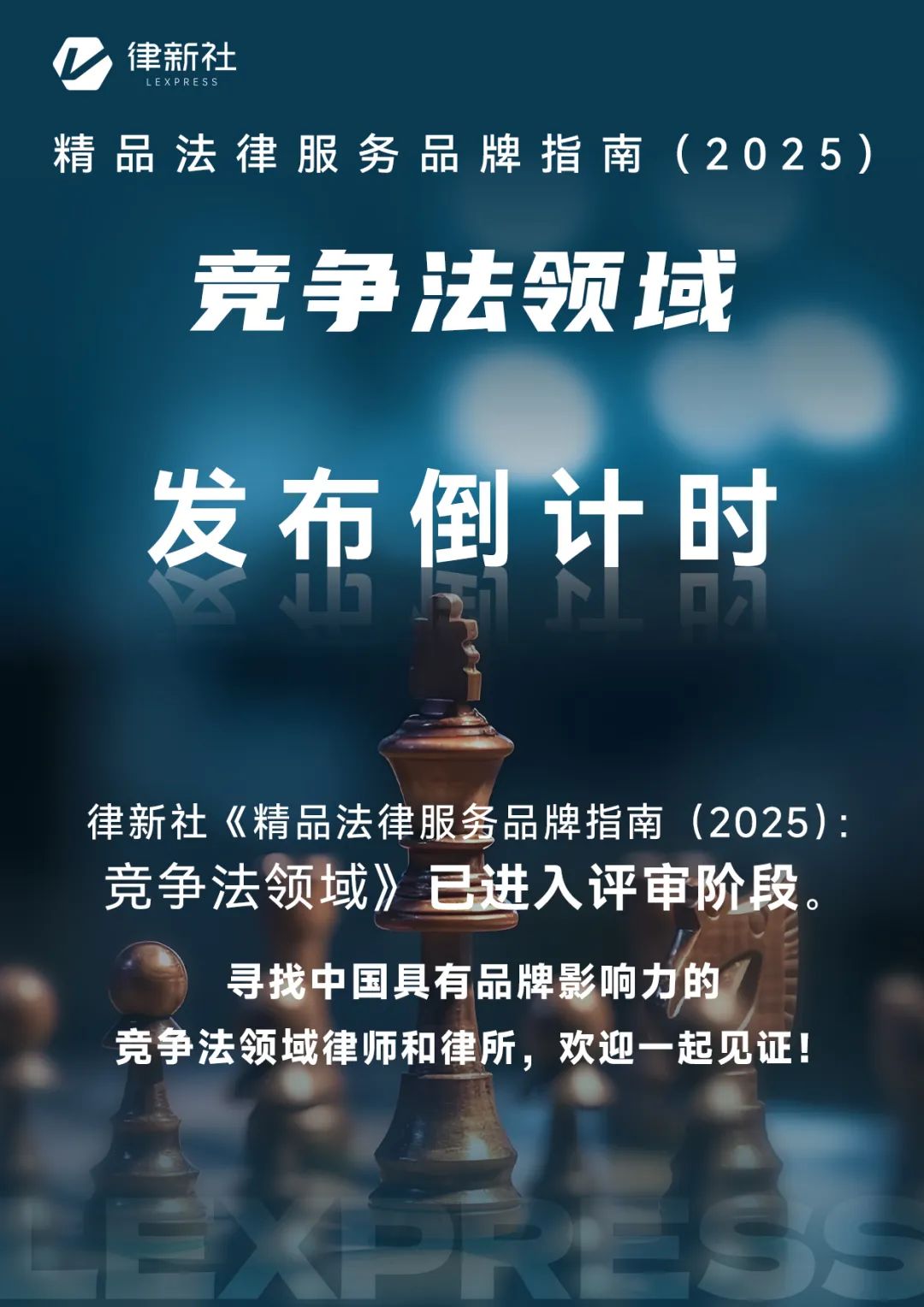作者丨律新社研究员 王思远 出品丨律新社研究中心 当竞争的硝烟蔓延至数据深海与全球赛场,当竞争的风云漫卷线上与线下、实体与虚拟经济,竞争法法律服务既是盾牌,亦是罗盘——它守护的不仅是企业的合规底线,更是市场经济的星辰大海。 当计划经济破冰遇上全球博弈,中国竞争法用四十年完成从“政策补丁”到“制度利剑”的蜕变。2024年国家反垄断局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数据显示:全年办结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11件,其中个案中最高罚没金额达到1.19亿元,医药行业通过执法推动涉案药品降价62%,金融数据领域首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处罚先河——宁波森浦案罚款453万元。最高法院2024年6月的新闻发布会公布,2013年至2023年,全国法院共审结垄断民事一审案件977件。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自2019年1月成立至2024年5月底,共受理垄断民事案件178件,审结131件,多起案件具有典型意义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公布反垄断指导性案例3件,发布了四批28件反垄断典型案例并均已纳入人民法院案例库。这些数字背后,是竞争法从1980年“竞争十条”的试探,到2008年《反垄断法》落地,再到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的跨越式发展。 2025年4月,律新社研究中心正式启动《精品法律服务品牌指南(2025):竞争法领域》调研。作为从事律师执业30年,深耕于竞争法与保险法领域,连续获评国际奖项并主导多起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多个标志性反垄断案件的行业影响力人物,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詹昊在接受律新社研究中心调研时对我国竞争法发展的进行了总结回顾,他指出中国竞争法法律服务正经历范式升级,中国竞争法律师需要同时精通法学与经济学,具备跨境规则协调能力。这场静默的变化,不仅关乎企业发展,更在重塑全球竞争的游戏规则。 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 管理合伙人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神州大地,中国市场经济的种子开始破土而出。四十年后,当我们站在全球竞争的十字路口回望,会发现竞争法的演进轨迹恰似一部浓缩的中国经济改革史——从早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试水,到如今深度融入全球治理的制度博弈,竞争法制度的每一次蜕变都折射出时代的脉搏。从1980年“竞争十条”[1]的破冰尝试,到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二次修订,中国竞争法法律服务在法治政策土壤的滋养下,完成了从“单腿跳”到“双轮跑”、从“国内合规”到“全球应诉”的跨越式发展。 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竞争法体系的首次“破土”。这部法律诞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阵痛期,重点规制仿冒混淆、商业贿赂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其立法逻辑更偏向于“市场秩序维护”而非“竞争机制保护”。当时的法律服务需求集中在传统商业纠纷领域,律师更多扮演“事后救火员”的角色。 2008年《反垄断法》的实施,则是中国竞争法体系的“成人礼”,也是中国广义竞争法体系的正式完备标志。这部被称为“经济宪法”的法律,首次系统引入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经营者集中审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现代反垄断制度。但相较于欧美国家立法史,中国竞争法的“双法分立”路径独具特色——先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填补执法空白,再以《反垄断法》构建宏观竞争框架,形成“自下而上”的立法补位模式。这种路径选择与中国渐进式改革一脉相承,但也导致早期法律服务需求呈现“重执法、轻合规”的特点。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反垄断执法呈现“九龙治水”格局:国家工商总局负责反不正当竞争和部分垄断协议查处,发改委监管价格垄断,商务部审查经营者集中。2018年市场监管总局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新组建的国家反垄断局整合执法资源,实现“一窗受理、全链条监管”。根据国家反垄断局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4)》显示:全年办结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11件,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643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72件。[2]又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数据统计,2025年前5个月经营者集中申报平均审查周期缩短至24.6天,体现出审批效能与市场活跃度实现双提升。[3]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詹昊在接受律新社调研时指出,《反垄断法》的出台,让中国竞争法从“单腿跳”转向“双轮跑”,企业需要同时应对微观层面的不正当竞争风险和宏观层面的垄断风险,法律服务从单一执法应对扩展到合规体系建设,从公共执法延伸到私人执法,甚至延伸到跨境协调。同时,过去这种分散的执法体系导致企业合规成本高企,律师团队需同时应对多部门规则差异,而执法机构的统一不仅提升了效率,更倒逼企业建立全流程合规体系,为竞争法法律服务的转向提供了契机。 此外,与欧美“司法主导、私人诉讼驱动”的模式不同,中国竞争法法律服务始终与政策导向深度绑定。相比中国“两法分立”的补位模式,欧美国家的竞争法体系更早实现一体化。美国以《谢尔曼法》为核心,并于1914年出台《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同时通过判例积累形成复杂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体现出私人诉讼在竞争法纠纷中的主导,欧盟则通过《欧盟运行条约》(TFEU)构建了统一竞争法框架。詹昊认为,中国竞争法立法的特点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但“补位”过程反而为企业提供了“缓冲期”。而随着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2024年《反垄断法》的修订,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私人诉讼正成为当下中国竞争法纠纷的重要解决途径。 如今,中国竞争法法律服务需直面全球化挑战,如何平衡本土政策与国际规则,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命题。 在反垄断风暴席卷全球的今天,企业竞争法服务需求正经历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从2013年茅台和五粮液因价格垄断被罚款4.49亿元的“破冰”案件,到2025年津药药业等四家药企因原料药价格同盟被罚没3.62亿元的“重典”,中国企业逐渐意识到竞争法合规不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正如詹昊在调研中指出,无论国企、民企,无论传统行业还是高科技领域,合规需求已呈现“全覆盖、全周期、全链条”的特征。这种转变背后,是企业从“被动应对调查”到“主动构建体系”的战略觉醒,更是竞争法服务从“边缘业务”到“核心刚需”的价值重构。 长期以来,国企因承担部分公共职能而被视为“反垄断例外”。但2019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长安福特纵向垄断协议罚款1.62亿元的案件,打破了这一认知。民企对合规的重视则源于“切肤之痛”,2021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因“二选一”行为被处以182亿元罚款,这一案例成为民企合规的“分水岭”。 反垄断罚款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倒逼企业投入。根据《反垄断法》,违法企业最高可被处以年营业额10%的罚款。这种“罚到痛处”的机制,使企业合规投入呈现“刚性增长”。主动合规正成为企业的“竞争护城河”。为此,詹昊指出,随着竞争法在执法、司法领域的不断强化,客户需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最初的不理解、不熟悉逐渐转变为理解和接受竞争法的重要性,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意识到竞争法执法和司法的广泛涉及;其次,企业从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加强竞争合规体系的建设,如医药、高科技、数字平台等行业开始建立竞争法合规体系;最后,企业认识到竞争法的严肃性和处罚力度,并且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海外诉讼和竞争法执法案件越来越多,对竞争法律服务的需求显著增加。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企业出海步伐加快,但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反垄断狙击。2021年华药集团维生素C反垄断案历时17年终审胜诉,成为中美反垄断博弈的标志性事件。该案中,美国法院最初依据“三倍赔偿”规则判决华药赔偿1.53亿美元,若败诉可能导致中国医药行业整体面临20亿元人民币的连锁损失。[4]类似案例近年在科技、新能源等领域频繁上演:2024年2月9日,欧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发布文件,称在一项关于DMA的诉讼中驳回了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对于暂停欧盟委员会将TikTok指定为“看门人”(gatekeeper)的申请;[5]2025年3月1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一项名为《与依赖外国对手电池脱钩法》(Decoupling from Foreign Adversarial Battery Dependence Act)的法案,将禁止美国国土安全部购买中国公司制造的电池,将对我国新能源企业造成威胁。[6]为此,詹昊在调研中亦强调,中国企业海外反垄断诉讼数量正逐年递增,涉及行业从传统制造业向数字经济、生物技术等高端领域延伸。中国企业往往低估了海外合规风险,例如欧盟DMA对“守门人”企业的严苛数据开放要求,可能导致中国科技公司丧失竞争优势。 由此表明,跨境竞争法法律服务的复杂性远超国内业务。詹昊指出,这些新兴领域具有集中、密集和创新活跃的特点,不仅我国竞争法需要加强关注如补贴政策、数据所有权和安全、以及数据作为“必需设施”时的开放等问题的应对。随着云服务的发展,数据领域的竞争关注度越来越高,竞争法律师也需进行前沿性研究,尤其需要对于产业前沿问题与竞争法的结合进行预先研究。 在竞争法法律服务领域,一场静悄悄的“能力变革”正在重塑行业格局。跨境诉讼从“被动应诉”升级为“主动布局”,法律服务的专业性门槛正以指数级提升。正如詹昊在调研中强调,安杰竞争法团队的许多律师同时具备法学和经济学背景,因为反垄断审查本质上是法律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博弈,反垄断立法的逻辑基础是市场竞争分析。这种能力需求的背后,是竞争法法律服务从“经验驱动”向“知识驱动”的范式转换—— 法学与经济学的“双料律师”成为行业标配,而全球化布局的“全球战队”则重新定义竞争维度。 在竞争法法律服务中,经济学分析已成为“必修课”。以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为例,执法机关需运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测算市场集中度,通过需求替代分析界定相关市场。意味着这种分析能力要求竞争法律师不仅精通竞争法的条文,更需掌握价格理论、博弈论等经济学工具。 此外,法学作为应用型学科,实践教育是连接理论体系与职业能力的关键桥梁。律师的庭审应变能力、客户谈判技巧及复杂案件解析水平,均需通过真实场景训练方能形成专业肌肉记忆。詹昊在接受调研时亦表示,中国法学实践教育仍处追赶阶段。尽管不少高校通过“法学+经济学”复合培养提升竞争力,但整体教育体系尚未形成标准化实践场景。 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热胀,中国律师在海外法律服务中的角色正经历从“陪跑”到“主导”的战略转型。在过去,中国律师多扮演“文化翻译者”角色,依托对中国市场特殊性的理解,在跨境诉讼中解释本土政策与制度。这种“文化解码”能力虽具不可替代性,但服务范畴仍局限于补充性角色。然而,随着国际化布局深化,中国律师开始突破“应诉支持”“地域陪伴”定位。通过设立覆盖“一带一路”关键节点的海外办公室来构建本地化服务网络;凭借对多法域合规的精准把握,将服务链条从个案应对延伸至战略咨询;更在跨国争议解决中展现对国际规则与本土实践的双重驾驭能力,逐步从服务参与者升级为规则协调者。然而,詹昊指出,虽然中国律师正在逐步站在全球的舞台展示自己,但是仍需要不断强化自身的能力。尤其是在多语种的口头表达和实际应用方面以及对国外法律制度、惯例的熟悉程度,在目前仍制约着中国律师在国际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力。 当竞争法服务的能力内卷从“专业跨界”升级为“全球博弈”,中国律师正以独特的路径重塑行业生态。“双料律师”的崛起,打破了传统法律服务的知识边界;“全球战队”的布局,则改写了国际竞争的规则话语权。正如詹昊所强调,未来的竞争法法律服务,本质上是法律智慧、商业洞察与全球视野的三重较量。 从法学与经济学的“双buff”叠加,到跨境服务中“中国价值”的凸显,这场内卷不仅是能力的竞赛,更是中国法律服务从“跟跑”到“领跑”的战略跃迁。在数据垄断、绿色竞争等新议题涌现的当下,中国律师的使命早已超越个案胜诉——他们正在用专业能力为中国企业全球化铺设合规轨道,用法律智慧为国际竞争秩序注入中国方案。 在数字经济与绿色转型交织的时代,竞争法服务正经历着“双重革命”:一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次修订将“内卷式竞争”正式入法,标志着中国从“事后处罚”转向“事前预防”的监管范式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数据垄断、绿色补贴等新兴领域的合规需求,正在重塑法律服务的底层逻辑。竞争法法律服务已进入“法律+技术+产业”的三维竞争时代,企业需要的不仅是合规方案,更是融合商业洞察的战略协同。这种变革既带来挑战——传统服务模式面临淘汰风险,也孕育机遇。 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标志着中国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从理念倡导转向制度刚性。新法第十四条明确禁止平台经济领域“低于成本价销售”行为,并将算法诱导、流量歧视等隐性强制手段纳入监管范畴,形成“行为模式+效果认定”的双重标准。这一立法突破不仅针对电商、外卖等领域的“自杀式补贴”乱象,更重塑了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则——企业价格行为需同时满足“成本覆盖”与“商业合理性”双重要件,迫使市场主体从“流量争夺”转向“价值创造”。面对新法、新规,詹昊表明,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有助于适应市场发展,填补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立法空白。但是对于“内卷式竞争”的立法规制仍存在概括式的特点,随着实践进步和技术发展,可能还需二次立法(或司法解释)来细化和明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 当竞争法法律服务从“合规工具箱”升级为“战略指南针”,新修法律正在重塑行业价值坐标系。“内卷式竞争”的立法突破,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技术颠覆传统竞争格局的当下,竞争法法律服务的命题,已从“解决问题”升维为“定义规则”——这既是挑战,更是中国法律服务行业的历史机遇。 中国竞争法已完成从政策试点到全球博弈的战略跃迁,其发展轨迹深刻映射中国经济转型与全球影响力提升。监管范式实现关键转型——从“事后处罚”转向“事前预防”,推动着市场生态从无序扩张转向秩序重构。法律服务行业随之升级,律师需兼具法学与经济学背景,服务从“灭火队”升维为“战略协同者”,中国律所通过海外布局从国际规则参与者蜕变为协调者,甚至是引领者。中国律师不仅守护国内市场公平,更以规则定义者姿态参与全球竞争秩序构建,在深化国际合作中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为中国企业全球化铺设合规轨道。 竞争法领域天高地广,竞争法的研究博大精深,有心有力的中国律师正在这一领域精耕细作;在国际竞争法赛场上,中国律师可能是个迟到者,但未尝不是后来居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