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源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专利代理师、知识产权团队副主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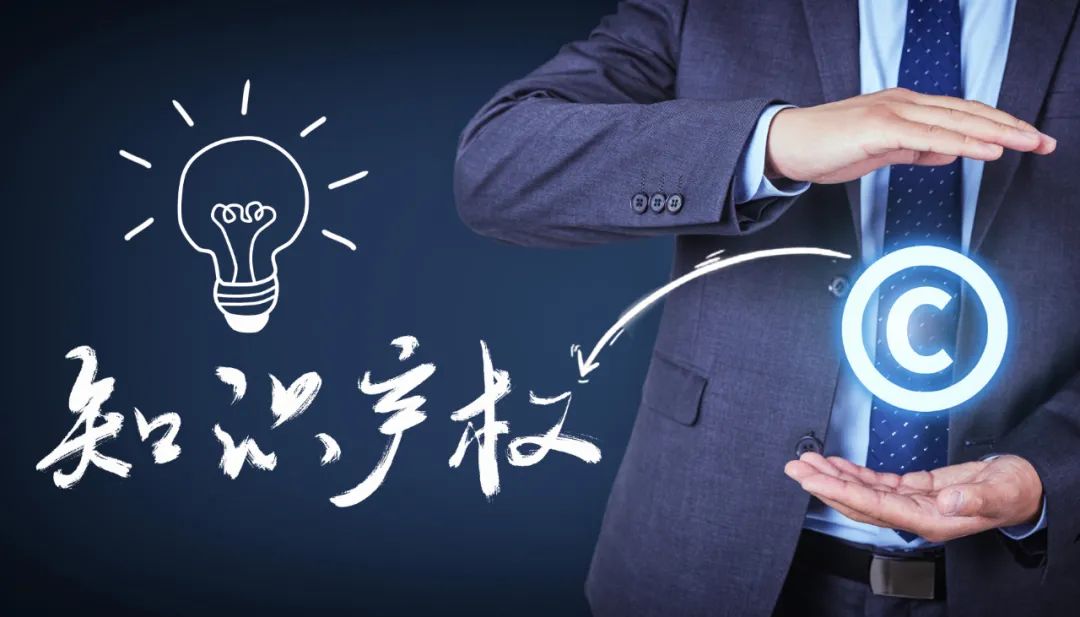
01
1、法律规定
《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种子法》明确规定了基数计算方法的先后使用顺序,即先按照实际损失确定,难以确定的按照侵权获利确定。
《著作权法》和《专利法》对基数的计算方法未规定先后使用顺序,即按照实际损失或者侵权获利确定,上述两者都难以确定的,《著作权法》参照权利使用费推定,《专利法》参照许可费推定。
各部法律关于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补偿性赔偿额)使用先后顺序的规定比较如下表: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十七条 | |
《种子法》 第七十三条 | |
《著作权法》 第五十四条 | |
《专利法》 第七十一条 |
2、案例分析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应该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获利为准,以权利使用费的合理倍数为参照,然而,计算基数往往会因为相关证据问题难以确定。《惩罚性赔偿解释》的第五条进一步明确了举证妨碍制度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方面的适用,人民法院依法责令被告提供其掌握的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原告的主张和证据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最高院于2021年3月15日发布的《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下称《典型案例》)列出的六个案件对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的计算方法如下表所示:
广州天赐公司等与安徽纽曼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562号】 | ||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米琪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2015)京知民初字第1677号】 | ||
1、以行政查获的侵权产品件数推定原告实际损失的销售量。 2、以阿迪达斯公司提供的2017年度会计报表认定阿迪达斯公司的毛利润率为50.4% | ||
《典型案例》列出的六个案件中,仅有一个案例采用参照商标许可使用费合理倍数确定计算基数。欧普公司与华升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原告提供了《商标授权许可协议》、《欧普照明发货托运单》、银行转账凭证以及“OPPLE欧普照明”商标授权店铺的现场照片等证据,法院认为,上述证据结合涉案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已经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据标准。
《典型案例》列出的六个案件中,仅有一个案例采用实际损失标准确定计算基数。阿迪达斯公司与阮国强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一审法院适用法定赔偿方式确定20万元的损害赔偿数额(含合理费用),二审法院则认为原告实际损失并未达到“难以确定”的标准,利用查明的事实,巧妙推测出原告的实际损失。
《典型案例》列出的六个案件中,有四个案例采用侵权获利标准确定计算基础。司法实践中的诸多情况下,专利权人的实际损失较难确定,这时就只能推定侵权人的侵权利润作为专利损失赔偿额。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该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关于侵权获利之“利”是营业利润(毛利润)、纯利润还是边际利润,各地法院存在争议。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2]

02
1、法律规定
《惩罚性赔偿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
因同一侵权行为已经被处以行政罚款或者刑事罚金且执行完毕,被告主张减免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在确定前款所称倍数时可以综合考虑。
显然,《惩罚性赔偿解释》仅规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计算的考虑因素,并未给出具体的计算方法,法院需要运用自由裁量权根据个案具体情况综合判定。因此,研习总结判例对惩罚性赔偿的倍数计算方法探究具有重要意义。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惩罚性赔偿解释》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惩罚性赔偿在民事纠纷领域独立适用,并不遵循“一事不再惩罚”。相反,已经被处以行政罚款或者刑事罚金且执行完毕的行为人仍然侵害知识产权的事实可以用来证明侵权人具有主观恶意。例如在广州天赐公司等与安徽纽曼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中,虽然侵权人已经在关联刑事案件中被处以罚金,但是最高院仍然顶格适用5倍惩罚性赔偿。
2、案例分析
《典型案例》列出的六个案件对惩罚性赔偿倍数的计算方法如下表所示:
广州天赐公司等与安徽纽曼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562号】 | 一审: 2.5倍 最高院: 5倍 | |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米琪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2015)京知民初字第1677号】 | ||
法院认为:正邦公司主观恶意非常明显,被诉侵权行为持续时间长,后果恶劣,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 ||
由上表可知,《典型案例》列出的六个案例中,有五个案例将惩罚性赔偿的倍数确定为2-3倍。在广州天赐公司等与安徽纽曼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中,一审法院也将惩罚性赔偿的倍数确定为2.5倍。惩罚性赔偿的倍数确定颇具“中庸之道”。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惩罚性赔偿倍数确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被量化。既然惩罚性赔偿倍数难以量化,很多原告直接主张5倍惩罚性赔偿,这无疑是将难题推给法官裁量。如案件满足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知识产权律师应当考虑诸多因素,参照相关判例充分说理后给出一个合理的倍数。这些因素主要包括:
行为人的主观状态;
侵权的情节;
损害后果以及侵权人的获利;
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如知名度、合理的许可费、侵权对整体产品市场的影响;
侵权人的偿付能力和判处的金额对侵权未来可能发生的影响。
惩罚性赔偿的量尺上目前仅仅出现了头部刻度“5倍”、中间刻度“2倍”和“3倍”,其它的尺度并未出现在《典型案例》中。鉴于各个典型案例之间的差异较大,头部刻度、中间刻度并不能得出情节严重程度和惩罚性赔偿倍数的对应关系。如何把握情节严重程度和倍数的对应关系尤待更多典型案例出现。
03
全面落实惩罚性赔偿对于知识产权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知识产权案件惩罚性赔偿基数计算方法已经由相关立法和《典型案例》加以明确,而惩罚性赔偿倍数计算方法尤待细化标准。现阶段,知识产权律师只能参照相关判例,充分考虑各个因素后推算出惩罚性赔偿倍数,然后依据“惩罚赔偿额=基数×倍数”给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方法。
附录:惩罚性赔偿立法大事记
《商标法》(2013年修正)增加了惩罚性赔偿条款;
《种子法》(2015年修正)增加了惩罚性赔偿条款;
《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修正)增加了惩罚性赔偿条款;
《专利法》(2020年修正)增加了惩罚性赔偿条款;
《著作权法》(2020年修正)增加了惩罚性赔偿条款;
《著作权法》(2020年修正)增加了惩罚性赔偿条款;
《民法典》(2020年公布)对惩罚性赔偿作了总括性规定;
《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2021年公布)细化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2021年公布)为惩罚性赔偿的准确适用提供参考。
# 注释 #
[1]《牛津法律大辞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06页
[2]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