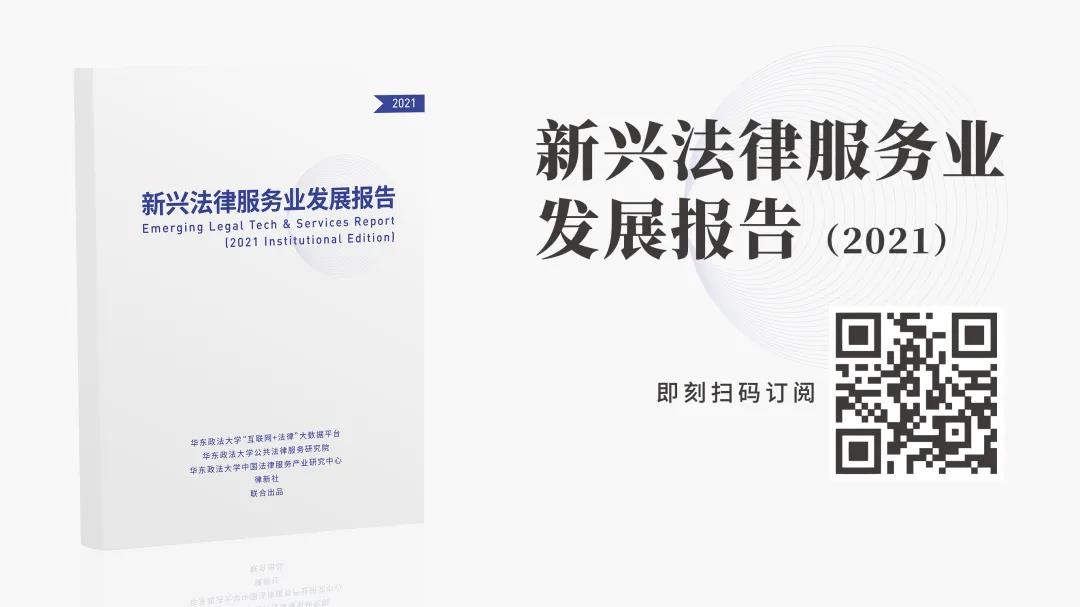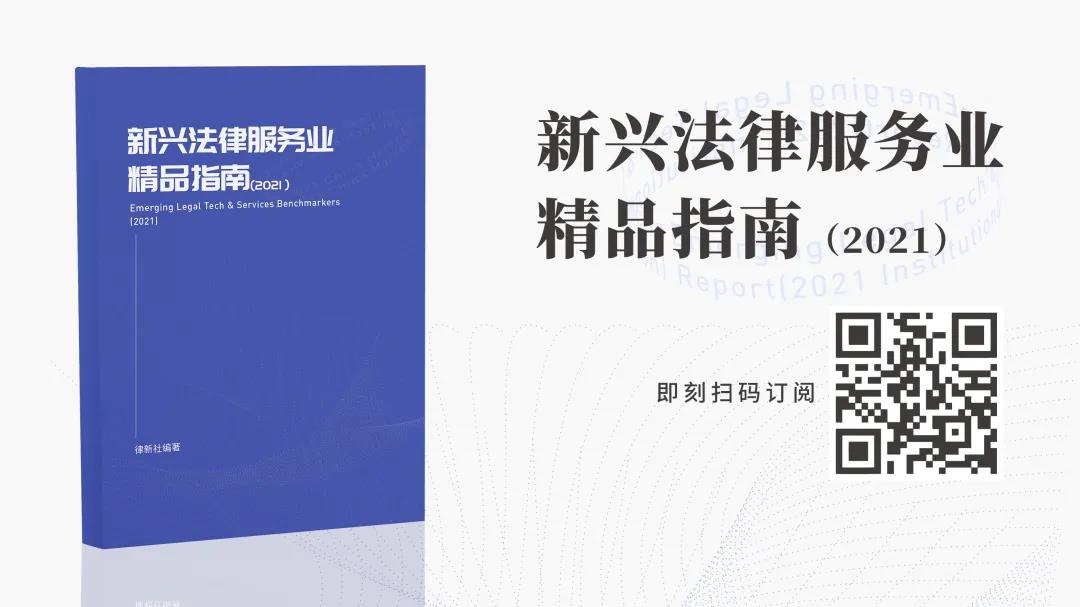作者丨凌清源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本科生
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兴起,自媒体介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刑事案件。
尽管从正当性来讲,自媒体介入刑事案件体现了言论自由与司法民主,“当公民基于公开的事实发表价值判断时,不论价值判断是何都不得被禁止”[1];从合理性来讲,自媒体介入刑事案件透露了民众惩恶扬善的朴素正义观,“在一定程度上说,民愤是否得到平息,是社会公正实现程度的一个尺度,也是刑罚目的实现程度的一个标志”[2]。
但是其弊端无法忽视。由于互联网巨大的传播力,刑事案件快速为大众所知,给案件当事人带来巨大社会名誉损失;甚至“以多数人的情绪战胜少数人理性”[3],影响司法公正,形成“多数人的暴政”。本文将以最近发生的阿里女员工事件为切入口,思考自媒体介入刑事案件弊端的法律规制。
01
7月27日,侵害事件发生
7月28日,女员工周某报警,警方出警,受理为刑事案件
8月2日,周某回杭州,向领导反应被侵害一事,领导回应:三天后答复
8月5日,周某向领导索要处理答复,未果
8月6日,周某在公司工作群、食堂曝光事件
8月7日,周某长文网曝:自身侵害
8月8日,警方第一次通报:案件调查中
8月9日,公司公布内部调查处理结果:涉事男员工被辞退,永不录用
8月10日,警方正式立案强制猥亵刑事案件
8月14日,警方第二次通报:案件嫌疑人王某和张某早已被采取强制措施
8月23日,王某妻子发声:我丈夫有错无罪,质疑周姓说谎
8月25日,警方第三次通报:张某涉嫌强制猥亵罪,正式批捕
9月6日,警方第四次通报:对王某终止侦查,不批捕,治安拘留15日
9月13日,王某妻子再次发声:周某利用他人善良作恶
后续结果有待报道……
从上述情节可以看出,当事人与民众的信息不对称是自媒体介入刑事案件弊端的根本成因,而流量导向的自媒体则趁机利用公众心理的弱点炒作舆论。
02
(一)当事人与民众的信息不对称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传媒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物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4]。完整的刑事司法程序耗时很长,这给了部分自媒体可乘之机。这部分自媒体并不了解案件的全貌,但难以抑制对流量收益的渴望,在信息不对称的黄金时间,利用民众负面对立的情绪煽动舆论,抢在司法程序之前对“恶人”完成一场 “审判”。
虽然一定会有许多颇有见地的民众不会轻易地为“议程设置”所左右,但是囿于网络时代信息爆炸的特点,这部分理性的声音极易被信息的海洋所淹没,甚至他们自己口中的话也会经历多道加工,完全地扭曲原意,成了 “他人有意的解读”。以百度为例,当你以“阿里女员工事件”为关键词在百度搜索时(如下图,2021.9.19搜索),你可以查到许多结果,但排在顶部的搜索结果,不论是“阿里巴巴女员工被侵害事件-百度百科”还是“阿里巴巴女员工事件的最新消息”都是加工过的二手资料了,民众无法直接地看到官方的发声抑或当事人的发言,探究真相的成本大大增加。因而多数民众迷失在了信息的海洋当中,不得不遵从网络上的“多数意见”。

(二)部分自媒体的流量导向
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发展壮大,自媒体所能带来的收益水涨船高,不少人开始将之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而自媒体所能带来的收益往往是与其所吸引的流量相挂钩的,商业利益驱使着各个自媒体走向流量导向,“促使大量背离传统新闻学的坏新闻出现:不核实、不准确、不公正、猜测、低级趣味”[5],而“一旦涉足司法案件,就难免出现超越司法程序、抢先报到的行为,从而对司法审判形成干扰”[6]。
若无有效的法律法规对自媒体的流量导向进行合理的规制,那么“劣币驱逐良币”则是市场作用下的必然结果——理性中立客观的被市场冷落,而充满情绪的收获越来越多的拥趸。
但现有的法律法规显然存在巨大漏洞。由于绝大多数的自媒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媒体,而是个人注册的账号,他们的言论在《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和改进案件报道的通知》等现行新闻相关法律法规语境下无法被解释为“新闻报道”。而调整全体公民社会关系的《民法典》《刑法》在“自媒体介入刑事案件”的情形中给予当事人的保护集中在名誉权、隐私权领域,且不论“基于公开事实发表价值判断”的“自由言论”无法被规制,仅从司法程序来看,此类侵权案件“告诉才处理”的高昂维权成本就足以打击当事人的维权热情,何况胜诉后的“赔礼道歉”的经济补偿较低,“消除影响”不能真正消除偏见。
综上,自媒体在流量导向的路上越走越远。
(三)民众自身心理的弱点
在网络上习惯了几十秒一次光电刺激的网民很难再有构建复杂模型以认识复杂社会问题的热情与耐心,在更多易得的“正反馈”下,探寻真相的“快感”显得成本高昂。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如今人们对于表达的渴望,“信息相对于过剩的时代,只有一种资源是稀缺的,那就是人们的注意力”[7],因此人们极易对错误信息进行二次传播,并且释放自身的负面对立情绪。
依照经验来看,社会舆论喜欢将复杂的社会事件转化为不同人群的对立,用简单架构认识复杂社会问题:张金柱、刘涌因官员身份被描绘成“滥用公权”者,形成“强者与弱者”对立的故事;而上文提到的阿里女员工事件则更是标签贴满,一度形成了对王某、对阿里、对山东地域文化一边倒的挞伐。
有些民众甚至完全将自己视作看客,将刑事案件看作用于娱乐的“谈资”:“在贪官下马时,关注其如何运用MBA知识管理多位情妇;对落网凶犯加封‘杀人狂魔’‘爆头哥’‘当代梁山好汉’等江湖之名”[8]。“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9]波兹曼所言是也。
03
(一)构建更加积极的司法公开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10]。传统理论认为司法公开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形式公开,包括立案公幵、庭审公开,案情公开,审判人员公开、审理过程公幵、裁判文书公幵、宣判公开、执行公开和审务公开;二是实质公开,主要是判决的事实依据公开、法律依据公开及其推理论证的过程公开等”[11],但笔者认为司法公开不仅仅有“公开”之义务,还应有“到达”之义务——对于可以公开且应当公开的司法信息,应当以方便民众获知的方式及时公开。
虽然从《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到《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司法公开的重要意义不断得到了国家、人们和学者的重视”[12],司法公开体系不断完善,但依旧存在对公开的信息重审判与执行、轻侦查以及公开的方式与民众常用的信息获取方式脱节的问题。
以阿里女员工事件发生的山东省为例,山东省在审判与执行阶段的司法公开的具体办法有:庭前公众号作开庭公告、法院官网网络直播庭审、网刊裁判文书、网刊被执行人员名单。而在侦查阶段的具体办法基本仅有警方各大平台的官方通报。仅从制度数量的比对就可以获知现有司法公开重审判与执行、轻侦查的现状。审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有司法公开重审判与执行、轻侦查的弊端造成当事人与民众长时间的信息不对称,给了舆论伤害当事人,乃至 “绑架”司法充分的时间。
又以山东省为例,对比司法公开的方式与民众常用的信息获取方式。山东省在审判与执行阶段以及侦查阶段的司法公开的具体办法如上文所述。而民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可以分为被动获取与主动搜索。被动获取主要是不带目的性地刷新好友的动态,查看各个搜索引擎的热搜;主动搜索主要是在搜索引擎上主动输入相关词条进行检索。囿于各法院官网、各地警方在各个网络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影响力较小,民众被动获取司法公开信息的可能性不大;又囿于上文提到的网络时代信息爆炸的特点,民众若要主动搜索,则将面对一片信息的汪洋大海。
由此,笔者建议参照日本制度,在刑事案件中由地方政府选拔具有高尚职业道德的新闻机构中的部分杰出记者,通过地方性法规授予其在刑事侦查阶段特许的报道权利(即“行业代表”制度),通过及时灵敏的媒体介入弥补司法公开在刑事侦查阶段的公开不足。
同时参照大型国家官方考试成绩公布时的查分系统在搜索引擎相关词条下置顶的方式,将可以公开且应当公开的“行业代表”的报导、警方的通报在立案侦查之后一段时间内在搜索引擎相关词条下置顶,方便民众了解案情,解决司法公开的方式与民众常用的信息获取方式脱节的问题。
最终结合二者解决当事人与民众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二)制定合理标准,将部分自媒体纳入新闻法体系规制
“由于量化评价管理是从经验论的窠臼中走出来的,它不以主观定性评价为依据,而是以自然科学泛式为理论基础,并追求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化,其本质是受科学理论或技术理论支配的,力图使量化评价像计量科学那样精密准确”[13],而社会科学理论所构建的社会模型依旧较为粗糙,诸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定性的社会科学模型较之“E=mc²”这种定性又定量的自然科学模型显得不太具体、不太直观,难以在较为微观的领域应用,显然定量社会模型的构建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法学也不例外。以刑法为证,一条法条其所述明的罪状往往较为抽象,对于一个犯罪具体的构成要件往往需要最高法予以定量的司法解释才能解决入罪标准的争议。在自媒体介入刑事案件领域我们也需要制定合理标准,对其进行定量管理。
如今许多的自媒体影响力已远超传统媒体,理应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国际社会主流的法律规制办法是将原本的新闻法体系扩大化,将影响力较大的自媒体纳入其中。美国将新兴媒体纳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管辖,依照34年、96年两部《通信法》进行规制;新加坡则通过政务部门调整,将多部门统一合并为信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IMDA),依照《广播法》和《互联网操作规则》对新兴媒体进行规制。
中国可以适度学习外国做法,以自身国情为基础,依据各个自媒体的所在平台、传播方式、关注领域、目标人群、注册主体,经过理论论证与实际试点,制定出合理的标准,将部分自媒体纳入新闻法体系规制,阻遏唯流量论。
(三)适用“红旗原则”于名誉权、隐私权领域
“在互联网领域,‘红旗原则’指如果对版权的侵犯事实显而易见,就像是‘红旗’一样具备明确性与显著性,那么网络服务商就应当主动对这种侵权行为进行制止,而不能以所谓不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为理由来逃避其责任。”[14]
民众负面对立的情绪是社会整体性问题,一时难以在根本上解决,但是依据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可以推论出友善良好的网络生态可以有效缓解这一问题。其中运营网络平台的网络服务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试想“红旗原则”打破版权领域的桎梏而运用于名誉权、隐私权领域——如果对名誉权、隐私权的侵犯事实显而易见,网络服务商就应当主动对这种侵权行为进行制止。通过对网络服务商的法律规制,可使其主动作为,打造友善良好的网络生态,缓解民众的负面对抗情绪,缓解舆论对当事人的伤害、对司法的干预。
其实对于“红旗原则”的适用我国有一定的法律基础,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但是这些法律法规都有一些问题,《条例》关注版权领域,未对名誉权、隐私权领域做出规定;《解释》属于刑事司法解释,实践中适用机会较少;《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在私法意思自治的语境下与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用户的举报权利结合作体系理解,是为网络服务者的被动义务。
运用“红旗原则”理论原理使网络服务商主动负担社会责任应当是法律研究的方向。
总之,自媒体介入刑事案件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有利有弊,我们需要有效的法律制度规制其弊端,发扬其长处。
# 参考文献 #
END
律新社品牌服务中心出品